
 |
开栏的话
译者与书相遇,在心灵共振中融以智慧、学识和情感,语言转换的同时,打开不同文化间互望之窗,成为文明进程中重要一环。经典重译,新作新译,字里行间,满是凝结的知识、无声的故事与文化沟通的印记。本版自本期起推出“译者·书”栏目,在译者的讲述中,品读翻译背后的故事,追寻文明交流的共鸣。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论〈马丁· 菲耶罗〉》中说:“在欧美的一些文学聚会上,常常有人问我关于阿根廷文学的事情。我总免不了这样说:阿根廷文学(总是有人不把它当回事)是存在的,至少有一本书,它就是《马丁·菲耶罗》”。
反复推敲,力求译文中西近似
大学三年级时,我们有一名阿根廷外教,选了《马丁·菲耶罗》作泛读教材。这部高乔史诗的内容和艺术风格吸引了我,于是便试着将一些诗句译成中文。时断时续,日积月累,到1979年,我总算译完了史诗的上卷——《高乔人马丁·菲耶罗》。同年,我有机会去墨西哥学院进修,就想在那里把它译完。恰好那里有几位阿根廷老师和学生,可以向他们讨教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两年后回国,基本译完了,只剩几个零星的难题未解决。幸运的是,我认识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的卡洛斯·阿尔伯托·雷吉萨蒙教授,他曾担任阿根廷国立科尔多瓦大学文学系主任,是研究高乔史诗的专家。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马丁·菲耶罗》的翻译,译完之后便束之高阁,从未奢望出版。
1984年,是史诗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150周年诞辰,阿根廷政府要展览各种文本的《马丁·菲耶罗》。我驻阿使馆与国内联系,希望尽快出版此书,送去参展。时间紧迫,只剩3个月了,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精装的《马丁·菲耶罗》(见右上图,资料图片)。这位用中文吟唱的高乔歌手在家乡受到热烈欢迎,阿根廷《马丁·菲耶罗》译者协会委托中国驻阿使馆文化参赞给我带来了译者证书和纪念银币。
1988年5月,时任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访华时参观北京大学,时任校长丁石孙将《马丁·菲耶罗》作为礼物送给他,总统立即说:“我邀请译者访问阿根廷。”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在西班牙主持翻译西班牙语版《红楼梦》。
《马丁· 菲耶罗》是我个人独立完成的第一部译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所幸在翻译过程中,我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追求译作与原作的最佳近似,既不生吞活剥,又不脱离原文,尽量求得“异化”与“归化”的和谐共存。首先是诗歌形式的近似。史诗作者是在模仿行吟诗人(流浪歌手)的即席演唱,采用的是西班牙语中最常见的每行八音节的民歌体,而且一以贯之,7200行都是八音节。但是汉语中极少有“八言诗”,而七言诗则非常流行,因此我决定用七言民歌体来翻译。原诗押韵,译诗自然也要押韵。既然是汉译,当然要遵循汉语诗歌的格律,否则会“水土不服”。仅以史诗开篇的6行为例:
我在此放声歌唱,
伴随着琴声悠扬。
一个人夜不能寐,
因为有莫大悲伤。
像一只离群孤鸟,
借歌声以慰凄凉。
这基本是直译。有一位学长曾建议我改为:
此时此地歌一曲,
吉他声声伴我语。
一生一世唱不尽,
苦难深深埋心底。
好似孤飞鸟一只,
我以此歌慰自己。
感谢学长的好意,但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原译。首先,原诗押“阿”(a)的韵,是开口音,适合吟唱;而译诗中的“曲、语、底、己”是闭口音,不适合吟唱。再者,就内容而言也和原诗有较大差异:如第一行,原诗中是“开始歌唱”,而不是“歌一曲”,且全书上下卷共46章,7200行,何止“一曲”。尤其是第三行和第四行,完全是译者自己的创作。我还是觉得自己的译文略好些,或许是“瞎妈抱个秃娃娃——别人不夸自己夸”吧。
跨越国界,诗歌翻译拉近人心
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新任驻华大使刚到任,他知道我是《马丁·菲耶罗》译者,便请我到使馆一叙。我将拙译送给他。大使很高兴,请我喝马黛茶,然后说:“赵先生,可否请你读一段,让我听听马丁·菲耶罗如何用汉语吟唱。”我说当然可以,便朗读了开篇这一段。他听了,兴奋不已,先是站起身,给我一个拥抱,然后想找一件礼物送给我,可事先又没准备,就从客厅橱窗的展品里,取出一把高乔人用的Facón(长匕首)送给我。我和他开玩笑说:“我们中国人送礼不送刀,一刀两断!”他笑着说:“诺,诺,我不仅不和你一刀两断,还要申请,叫我们的总统为你授勋呢!”
他果不食言。1999年,译林出版社将《马丁·菲耶罗》收入世界英雄史诗译丛。阿根廷驻华使馆为新版中译本《马丁·菲耶罗》举行了首发式,并借此机会为我颁发了由总统签发的骑士级“五月勋章”。
2008年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出版社采用我的译本,出版了西班牙语、英语、汉语三语版的《马丁·菲耶罗》,不仅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引起了阿根廷外交部的重视。他们立即购买了1000册,并愿意支持出版羊皮烫金封面的豪华三语版《马丁·菲耶罗》,作为馈赠各国贵宾的礼品。
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马丁·菲耶罗》译者协会主席戈麦斯·法利亚斯先生编了一本《孔子和马丁·菲耶罗》,将史诗中的格言与《论语》中的孔子语录进行对比,虽然有些牵强,却可以看出作者对史诗的热爱和对中华文明的崇敬之情。
2009年,因翻译《马丁·菲耶罗》,我有幸认识了阿根廷著名诗人胡安·赫尔曼,并推荐他参评获得首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赫尔曼不仅是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还是令人尊敬的革命斗士。他曾任新华社特聘记者,两次应邀访华。当周恩来总理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说“想走长征路”,并真的沿着红军足迹完成了自己的“长征”。在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期间,我们成了好朋友。临别前,他为我写了一首题为《青海湖》的诗。
2011年,我邀请阿根廷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罗贝托·阿利法诺参加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自1974至1985年,罗贝托作为博尔赫斯的助手,和他一起从事翻译工作。回国后,他在阿根廷《民族报》上撰写题为《伟大的诗歌节》的文章,借用秘鲁作家略萨的话赞美中国:“这是一个现代化的、信心百倍、繁荣昌盛、真正的21世纪的国家,其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举世瞩目。当今世界依然挣扎于贫困、被边缘化和缺乏安全感之中,而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堪称全世界的榜样。”
从青海回到北京后,我陪同罗贝托游览了长城和故宫。当他知道秘鲁里卡多·帕尔玛大学邀请我于当年10月去做关于巴略霍诗歌翻译的讲座,并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时,一定要我顺访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样做一个关于翻译《马丁·菲耶罗》的讲座。我欣然接受,这正好弥补了我当年未能访问阿根廷的缺憾。在阿根廷作家协会大厅,上百位阿根廷诗人、作家和文化界人士济济一堂、聚精会神,听我讲汉西两种语言的对比以及我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在听讲座的人中,有一位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告诉我,第二天,他在课堂上说起此事,一位学生对他说:“老师,我外公有一位中国朋友,也翻译了《马丁·菲耶罗》。”原来,这位学生的外公就是雷吉萨蒙教授。我很快就和教授的女儿莫妮卡联系上。2012年,莫妮卡和姐姐以及一名同事来华旅游,我请她们到家里做客并参观北京大学。无论对她们还是对我,这都是终生难忘的惊喜。
通过翻译《马丁·菲耶罗》,我深深体会到,语言是使人心相通的桥梁,而翻译就是在搭建沟通心灵的彩虹桥,能为其添砖加瓦,译者一生都会感到幸福和欣慰。
赵振江,1940年生。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会长,曾获西班牙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和智者阿方索十世勋章、智利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等。2004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曾获中坤国际诗歌奖、鲁迅文学翻译奖等。主要著作有《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译著有西班牙语版《红楼梦》与西班牙语诗选20余部。
版式设计:蔡华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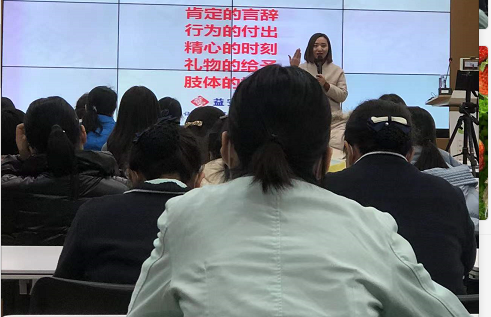













Copyright 2015-2022 亚太知识产权网 版权所有 备案号:沪ICP备2020036824号-11 联系邮箱: 562 66 29@qq.com